在当前合伙型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架构设计与员工股权激励实践中,有限合伙人(LP)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投资目标公司,已成为行业内广泛采用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作为间接投资者的有限合伙人,能否突破其“间接持股”的身份限制,绕开持股平台这一中间层级,进而直接向目标公司主张股东知情权,正逐渐演变为实务操作中亟待厘清的核心问题。
一、司法实践的裁判分歧
目前各地法院对有限合伙人直接向目标公司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审理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存在以下两种主流观点:
(一)反对观点:严格坚持权利主体资格
滕某诉A公司案 【(2024)沪0104民初20319号】
案件概要:
本案中,滕某为B中心(有限合伙)、C中心(有限合伙)股东,B中心(有限合伙)、C中心(有限合伙)系A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滕某通过EMS邮寄知情权申请书的形式,向A公司、B中心(有限合伙)、C中心(有限合伙)邮寄了相关知情权申请书原件遭拒收并退回;又向对方邮箱和负责人手机发送了知情权申请书,也未得到答复;后以报警的形式进入A公司办公场所要求履行股东知情权亦遭拒。因无法知悉A公司的情况,滕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行使股东知情权,了解A公司的实际情况。
法院观点: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亦可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该权利系公司法赋予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行使该权利的首要前提系股东身份的确认,只有被公司正式登记在册的股东,才有权行使相关的股东知情权。
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滕某既未被登记在A公司的股东名册或章程中,又未被登记在该司的工商资料中。本案中,滕某亦明确其仅为系B中心(有限合伙)、C中心(有限合伙)的股东,而A公司的股东包括B中心(有限合伙)、C中心(有限合伙),故其系间接股东。
综上,滕某在本案中要求对A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蒋某诉新垦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案 【(2021)京02民终5708号】
案件概要:
本案中,卞某、北京X灵、天津X灵为新垦粮公司股东,蒋某系天津X灵的有限合伙人之一,于2011年8月6日与×灵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北京公司,为天津X灵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查伊培签订《入伙协议》。2019年12月24日,蒋某向X灵北京公司发出《通知函》,要求其履行两项义务:1.于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切实采取措施维护合伙企业及合伙人的合法权益;2.提供全部投资项目相关资料。此后,蒋某认为X灵北京公司怠于行使股东知情权,诉至法院。
法院观点: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的内容,股东知情权是基于股东资格而产生的股东权利,系为股东提供了解和监督公司经营管理情况的合法途径。股东身份是行使股东知情权的前提。蒋某不是新垦粮公司的股东,亦从未持有该公司股份,故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行使股东知情权的权利基础。
其次,天津X灵系有限合伙企业,X灵北京公司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不属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不应直接适用公司法。且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行使股东知情权作了上述特别规定,蒋某不符合该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六)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该规定对提起诉讼针对的主体作了明确规定。蒋某作为天津×灵的有限合伙人之一,可以依据该规定主张权利。即使蒋某依据该条款第(七)项提起诉讼,亦应在该法条的范围内主张权利。蒋某依据合伙企业法直接提起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股东知情权诉讼,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二)支持观点:在特定条件下认可穿透行权的必要性
林某等六人诉A公司案 【(2025)浙0110民初7907号】
案件概要:
本案中,丁某及B公司为A公司股东,原告林某等六人为B公司有限合伙人,金某为B公司普通合伙人。2019年起,A公司涉多起纠纷被诉(包括金融借款合同、租赁合同等),且因A公司拒不履行又未报告财产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消费。
2024年12月2日,六原告向B公司致函,要求B公司提交合伙事务执行情况及A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金某回函并后附有移交清单数份。六原告收到金某的回复意见后,向A公司发出《股东行使知情权申请书》。六原告认为,A公司经营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已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而B公司作为持有A公司48.0564%股权的股东,其执行事务合伙人金某怠于行使作为执行合伙人的义务。因此,其他各合伙人有权依据《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及《公司法》相关规定,代B公司申请查阅并复制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资料。该申请书均被退回后,六原告起诉至法院。
法院观点:
本案中,第三人B公司设立前,六原告均为被告A公司的股东,第三人B公司设立后,六原告将各自持有被告A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第三人B公司,由第三人B公司持有被告A公司的股份。因此,第三人B公司实质是全体合伙人间接投资被告A公司的持股平台,其收益来源于被告A公司。六原告要了解第三人B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必然要了解被告A公司的具体情况。当第三人B公司的合伙执行事务人金某经六原告通知怠于行使权利时,六原告代向被告A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这一基础性股东权利,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综上,六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
二、有限合伙人派生行使知情权的法律要件分析
结合现有判例,笔者认为目前人民法院对于有限合伙人能否穿透行使股东知情权的审理通常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行权基础
股东知情权作为特定主体享有的权利,具有极强的身份属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前提应是原告起诉时或至少曾经具有“公司股东身份”,因而有限合伙人不应被允许轻易穿透行权。
举例而言,在(2024)沪0104民初20319号、(2021)京02民终5708号案件中,徐汇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均以“股东知情权是基于股东资格而产生的权利”,股东身份是行使股东知情权的前提,而原告并未登记在股东名册、章程或工商资料中,亦从未持有该公司股份为由,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且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亦明确,即便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内容进行起诉,亦应在第六款规定“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的范围内主张权利,而非直接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
相关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七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
(二)行权前提
有限合伙人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前提应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且该诉讼目的系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
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需要注意的是,股东知情权主要用于解决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怠于行权”并不简单的与不作为挂钩。如执行合伙人本身是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大股东等,其天然便对相关情况知情,这一观点在(2020)粤0305民初24554号、(2022)浙1002民初1062号案件中也得到了法院认可。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认为,作为崇隆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王某同时亦是骏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需查阅或复制相关资料亦能够清楚知悉骏业公司的情况,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因此无法得出有限合伙人可以借此查阅或复制相关文件的结果。而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更是以“苏某发函要求暂停出售盛灿合伙企业持有的中欣公司股份,或要求向其提供盛灿合伙企业的相关材料,该行为虽能反映出苏某在主张知情权,但并不能反映出系因第三人的知情权受损害,苏某为此督促行使其权利”为由,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第六十八条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一)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伙;
(二)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
(三)参与选择承办有限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四)获取经审计的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
(五)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六)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
(七)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八)依法为本企业提供担保。
(三)行权利益归属
此外,派生诉讼的制度初衷在于维护合伙企业的整体利益,而非有限合伙人的个人利益,诉讼带来的任何利益皆应归属于持股平台。若有限合伙人想达到的诉讼目的系满足自身知情权所需,则不应允许其穿透行权,即便允许其穿透行权,也不应同意其直接向有限合伙人交付资料的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2020)京0108民初15359号案例的观点中提到:因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的目的限定于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即诉讼请求的受益主体应为合伙企业本身。恒天公司虽以自己名义提起派生诉讼,但其不能要求对方直接向自己履行交付资料等义务,诉讼请求利益实际归属于第三人岁兰智联合伙。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在(2023)京0107民初5887号案例中也明确指出:股东知情权作为股东的专属权利,与公司的资合性、人合性密不可分。通过代表诉讼的方式,在知情权方面达到类似“揭开公司面纱”的效果,只会对公司的资合性、人合性带来严重不利影响,甚至撼动公司法的基本制度。郭某作为某公司的合伙人,若某公司或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履行相关股东权利导致其受到损失,现行法律、法规并不排除郭某的救济途径。
退一步讲,即便有限合伙人在知情权方面,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诉讼,首先,要证明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合伙企业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且不行使相关权利严重影响合伙企业的利益;其次,要证明存在内部治理失灵的情形。郭某作为某公司的合伙人应当先行启动内部救济程序,只有在合伙企业内部治理失灵的情况下,才可以为维护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诉讼。但基于现有证据,郭某显然并不符合前述情形。
最后从本质上讲,此类型的诉讼出发点与落脚点仍在于维护合伙企业、公司等组织体的利益,故而胜诉利益应当归属于组织体。但在本案中,郭某却欲通过诉讼主张享有相关利益。因此,郭某主张对某公司行使知情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前文中提及的(2020)粤0305民初24554号案件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中亦指出本案诉讼系为原告满足其自身知情需求而提起,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为了本企业的利益”提起诉讼的情形。股东行使知情权涉及公司管理成本及公司商业秘密,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需要兼顾公司利益,正是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对股东知情权诉权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即该诉权专属于公司股东。该限制已系司法解释为平衡各方利益所作出的安排,不应随意突破。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涉案合伙协议已对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享有的知情权作出了规定或约定,如林某认为其合伙人知情权受到侵害,其可通过向崇隆企业主张权利等方式寻求救济。故本案不应以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方式,突破前述司法解释对股东知情权诉权的限制性规定。
三、穿透行权对各方主体的潜在影响
(一)对目标公司的影响:
诉累增加
目标公司将面临来自多层结构(登记股东、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请求或诉讼,增加了应诉成本和对经营管理的干扰。
商业秘密泄露风险
在法院支持穿透行权的情形下,公司的财务账簿、交易文件等敏感信息将被更多主体知悉,保密链条被迫延长,泄露风险相应增大。
治理秩序受扰
穿透行权挑战了传统上公司仅需对登记股东负责这一原则,使公司陷入需要判断持股平台内部合伙事务(如执行合伙人是否怠于行权)的困境,干扰正常公司治理秩序。
(二)对持股平台及执行合伙人的影响:
执行合伙人履职风险与压力
执行合伙人将面临被有限合伙人挑战其“怠于行使权利”的风险。其所作出的任何关于是否以及如何向目标公司行使知情权的决策,都可能被重新审视并产生诉讼。
合伙协议效力受限
随着部分司法实践支持穿透行权,一定程度上削弱持股平台内部《合伙协议》关于信息传递、权利行使等安排的约定效力,有限合伙人将更加倾向于绕过协议约定直接寻求司法救济。
有限合伙人关系管理复杂化
执行合伙人需要更审慎、更及时地处理有限合伙人的信息请求,并做好完整的书面记录,以证明自己并未“怠于行使权利”,增加了管理成本和复杂度。
(三)对有限合伙人的影响:
提供了权利救济的新路径
部分司法实践支持穿透的案例为有限合伙人提供了一条可能的救济途径,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底层资产的投资监督能力。
行权成本与行权的不确定性
穿透行权需满足严格的前提条件(需证明执行合伙人怠于行权、为了企业利益等),有限合伙人提起此类诉讼将面临较高的举证责任和败诉风险,结果却仍具有不确定性。
四、结语
综上而言,有限合伙人能否穿透持股平台直接向目标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在目前司法实践中仍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法院裁量倾向于围绕前文提及的行权基础、行权前提以及行权利益归属三方面进行审慎审查。
这一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也提示了市场各方,相较于事后依赖司法裁量,事前的协议安排和规范治理更为重要和可靠。对于执行合伙人,勤勉履职并完善内部信息沟通机制是规避风险的关键;对于有限合伙人,投资之初即在《合伙协议》中设定清晰的权利条款是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对于目标公司而言,坚守公司治理原则并完善章程中的防御性条款是应对之策。只有清晰的规则和良好的契约精神,才是平衡各方利益、减少此类争议的根本之道。
-
luxuan@hengtai-law.com
-
021-68816261
-
Corporate and M&A/Dispute Resolution/Intellectual Property/Family Law/Labor and Employment
-
Chinese、English

-
zhanghaonan@hengtai-law.com
-
021-68816261
-
Dispute Resolution/Labor and Employment
-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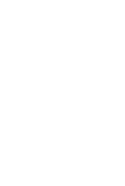

-911.jpg)